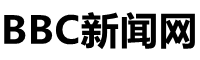本篇文章4651字,读完约12分钟
作者:张余思毅
“你将如何度过妇女节?”
当岳把这个问题抛给身边的几个职业女性时,答案几乎都与她们的工作和职业密切相关。
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。根据联合国官方网站,“今天,妇女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肯定,无论她们的国籍、种族、语言、文化、经济状况和政治立场如何。”
今年的这一天注定不同于过去。在COVID-19中的肺炎流行病已经席卷,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正面临着动荡和变化,许多妇女也面临着她们身份的叠加或转变。
但我们看到的是,在这种流行病下,女性产生了巨大的能量。他们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坚守岗位;或者用你的力量去帮助别人,修复由流行病造成的伤疤...
以下是几名在疫情期间工作的妇女的自我报告。其中有支持武汉的医务人员,为武汉奔走的志愿者,化身为主播的人民教师。她们不仅是她们,也代表了所有在疫情中发挥自身价值的女性。
梅长宁,武汉收容所的护士
新华社,避难所里的医务人员
我是山东省一家公立医院的护士长。2月9日,我来到武汉,支持收容所的医疗服务。
根据时间表,我将在3月7日下午22: 00进入机舱,第二天早上4: 00离开机舱,这是我在妇女节的工作。作为这次被派往武汉的护士长,我和团队的其他领导会给每位女性同胞一支口红。
我记得疫情爆发后,我和我的家人看到了山东对口支援黄冈的消息。当时,我的岳母以极大的热情对我说:“宁美,如果医院需要它,你必须报名。”不久之后,我接到了领导的电话,要求我组织每个人报名参加这次任务。
我是这个部门的护士长,唯一的党员,还有几个年龄较大的部门成员,其余大部分都是小女孩。我必须对他们负责。当我把小女孩送上战场时,我怎么能告诉他们的父母呢?所以我想都没想,就报了名。
来到武汉后,我意识到我真的在战斗。
这是负责船舱的护理工作。在去避难所之前,医生和护士应该提前1小时45分钟集合准备出发,因为额外的时间用来穿防护服。我们都穿手术服,然后穿防护服,外面穿隔离服,然后戴帽子和n95口罩。我是近视眼,我需要在戴眼镜的基础上戴一副护目镜。呼吸很困难,也很难抑制。

脱下我们的防护服需要一个多小时,因为我们被病毒覆盖并且更加小心。在这10个小时里,我们不能吃喝,更别说大小便了,所以在进入机舱之前,我们应该严格控制饮食,穿尿布。
我刚进船舱的时候没有经验,穿的衣服有点多。当我离开船舱时,汗水流到脚踝,衣服从领口到裤腿都湿透了。后来,当我有了经验,我穿少一点在里面。虽然有点冷,但我能保持头脑清醒。
以前,一些女同事向我要药来推迟生理期。因为在避难所里,即使在生理时期,我们也不得不忍痛抵抗。我告诉她我们可能要在武汉呆几个月,我们不能每次都用药物来推迟生理周期,这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。
但是在避难所里,身体上的困难很容易克服,心理上的挑战更难。我有一个处于崩溃状态的队友。我经常启发她,但我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,因为我们总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中。
我有良好的心理素质。一天晚上,我非常想家,很想我的女儿,所以我只是在我家的后面走了一圈来平静我的情绪。
我最感动的是,在我们负责的地区有一个9岁的女孩。她的父母没有和她在一起,因为她的整个家庭都感染了COVID-19肺炎,并且因为不同的情况住在不同的医院。当我看到她时,我想起了我的女儿,她比她大一点。我想我离开了我的女儿,来到武汉正是为了让她尽快与母亲团聚。

当小女孩离开小屋时,哭起来真的很痛苦。当我把她送出船舱时,她哭着对我说了一句话。她说:“我会取代武汉,谢谢你。”每当我想起这件事,我就感到很不舒服。一个9岁的女孩应该在父母的怀抱中被宠坏。
在收容所的这段工作经历应该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亮点。事实上,我当护士已经14年了。虽然这份工作很累,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一天。
这次我为孩子们感到抱歉。我想在疫情爆发后多陪陪他们。过去,他们经常求我陪他们,但我总是和他们打交道,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时间。
左志红,一名女性防疫志愿者
2月9日晚,左智宏和女儿回到广州后的第18天第一次外出,就是为了得到朋友赠送的急救口罩。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过去,妇女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,祝福大多在我的心里,这可能无法表达。今年的妇女节有一种灾后重生的感觉。我将特别祝福我的母亲和其他长辈,我的嫂子和其他同龄人,女学生和老师以及我家乡的姐妹们。他们住在疫区不容易,所以需要特殊照顾。

这种流行病激起了我们每个人。3月5日,我在广州的家里回忆起这件事,我仍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。
今年春节回家早在去年12月初就计划好了。毕竟,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乡过春节了。此外,小学、中学和大学都在武汉,我的朋友分散在世界各地。只有春节在一起。
在离开之前,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老家过春节。但在咨询了在家乡医院工作的二哥后,他说:“问题没那么严重。”我还搜索了公共信息,所有人都说:“这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,没有人可以传递。”。我放松了警惕,1月19日,我开车带着我9岁的女儿和同学回到了武汉郊区的家乡。

1月20日,当钟南山说出“人际传播”的真相时,我恨自己不能马上回到广州,但不到一天就离开似乎太不合理了,我不能告诉父母。我对自己照顾得很好,从不出门,并且把我的旅行从第一个月的第五天提前到第一个月的第一天早上。

1月23日一大早,“武汉10点关门”的消息就出来了,我傻到整夜睡不着,迫不及待地想长出翅膀,飞离武汉。
早上八点钟,我的父母为我担心。我的二哥在医院上夜班,不能休息,争分夺秒地开车送我和女儿去咸宁乘高铁。一路上,我快速查询了交通信息,买了高铁车票。我被恐慌和内疚包围着——我的亲戚和朋友会生病吗?当我有危险的时候,没有他们我能逃走吗?原谅自己,带走孩子...

对于从未经历过的人来说,很难体会到和平时期像战争一样逃离的感觉。1月23日,在从父母家到我回广州的几个小时里,我的眼泪一直没有干,我不得不耐心地向哭泣的女儿解释为什么我不能吃年夜饭,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的家人。

当我回到广州隔离时,我每天两次向社区医院报告我的体温,悲伤时有发生。大学同学的父亲因病去世,但她不能回去为她送行。她在电话里哭了。我的二哥也被转移到COVID-19指定的肺炎医院,再也没有回家。我的亲戚和同学的家人都听到了生病的消息,我每天都很担心。

我能做些什么来为家人和朋友的安全祈祷呢?
回到广州后,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广州校友会副秘书长,我被带到了广州校友会防疫捐赠工作小组。我看到几十名校友跑来跑去为疫区筹集资金,购买防疫物资,满足医院的需要,并移交后勤工作。我很感动,用我微薄的努力做了一些捐赠和宣传工作。

经过一周的隔离,人体没有出现任何异常,他的心脏稍微安全了一些。2月初,我在微信群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求医信息。我对自己说,我应该振作起来,做更多的工作。
当我静下心来推断发生了什么时,我认为信息的封锁与流行病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。
2月4日,我咨询了一位在母校宣传部工作的妹妹。学校是否建立了一个平台来收集校友及其家人的信息以寻求帮助?师妹说没有这回事。在与学校老师的沟通得到肯定后,我开始注意总结这类信息。
2月5日,我从另一位师姐那里得知,她在央视工作的同学可以帮助危重病人找到床位。我充满动力,从各个校友团体收集和核实信息,然后交给她。第二天,我了解到《人民日报》也有在线提交渠道,所以我同时将收集到的数据提交给了《人民日报》的校友。

三天前,我自己检查了信息汇总表,我能够应付。随着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,寻求帮助的案例越来越多。
2月7日,在北京春晖修女的建议下,我成立了一个急诊床位安排小组,招募了近十名热心的校友,收集整理危重病人的信息,帮助他们找床位。2月8日,武汉校友会派出骨干增援,并带来数十名校友志愿者,将我们的团队扩大到近100人。

我们从公共渠道梳理出各种帮助方式,包括120、110、社区帮助电话等。,有序推进抢救工作,包括收集患者信息、协助填写表格、通过各种渠道提交表格等。
从2月4日到2月20日,我们抢救了320多名危重病人,其中大部分得到了妥善治疗。
在抢救危重病人的过程中,我被许多志愿者的善良、热情、坚韧和能力所感动,尤其是来自武汉的孙老师。
她不仅动员了许多学生和她的儿子做志愿者工作,而且还亲自送来了援助物资。她孜孜不倦地跟踪和抢救危重病人,并帮助了许多病人。后来,我偶然得知孙老师的哥哥也病了,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。
孙老师曾哽咽着告诉我,二月五日是她丈夫去世十周年。当时,她的哥哥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,她的心很痛。她什么也帮不了,但她致力于志愿工作。“如果我不能帮助他,我会尽力帮助别人。”。
欧阳女士,一位教了13年书的女老师
欧阳女士正在备课,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我是湖南一所县公立学校的初中英语老师。除了给三个班的孩子上英语课,我还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。
今年1月31日,湖南省政府首先通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,开学时间不得早于2月17日,第二次通知说学校不能在3月2日前开学,然后通知说开学时间的推迟要视情况而定。
当我第一次听说学校延期时,学校并没有统一要求现场上课,但我给了我的同学们几堂现场课。寒假以来,我为班里的学生制定了寒假计划,希望能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。
在五六次家庭作业现场讲座后,学校开始统一安排现场直播。
事实上,在线资源相当丰富。在开始“云学习”之前,学生可能不会接触到这么多学校的在线教学资源。我了解到有一个网站有利于学生的英语学习。尝试之后,我在三个班级为自己和孩子们注册了账户。
有些人可能会认为,如果我在这个网站上为学生开一个账户,那是没有必要的。我该怎么说呢?教书13年后,我开始进入这个行业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喜欢教孩子。直到现在,我仍然非常爱学生,我希望他们从我认为好的事情中受益。

对我来说,网上教学的最大挑战是我不能准确掌握学生的状态和学习效果。我认为课堂很有趣,也很有感染力,但是通过互联网与学生的互动很少。
为了尽可能避免枯燥的课程,我现在用面具展示我的脸,并插入像“金蛋彩票”这样的游戏,希望他们能多加注意。
我会更加注重网络课程的效果,所以我会尽力突破教案,让课堂内容更加有趣和丰富。此外,“云教学”的挑战主要在于我作为班主任的课堂管理责任。作为班主任,我们应该督促学生打卡——健康卡和晚自习卡;我们还需要检查课程。我们需要统计每节课没有达到30分钟的学生,然后通知并督促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看重播,并与家长沟通询问原因。这些事情会让我觉得累。

开始上网络课的头几天,我的声音都沙哑了。现在好多了,因为现在我要一起讲解三个班的英语课。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打不赢“麦巴”州。我过去能在ktv里连续唱很多歌。现在我不会唱歌了。有时候我女儿在激烈的时候会感到受伤。

说到我女儿,我感到有点内疚,因为她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,成绩也不太好。在学校里,无论从班主任还是从教学的角度来看,成绩都是非常耀眼的。但是我的家人和朋友会说,“你是怎么把你的学生管理得这么好的?你为什么不多关心一下你的女儿呢?”

虽然我现在在家工作,但是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和我的孩子在网上,但是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我的学生在一起。包括今天晚上(指3月5日,采访的那一天),我也会给学生们打一个视频电话,给他们听写。
今年3月8日的妇女节是星期天。在前几个星期天,我一直在批改学生的作业或准备课件,抄教案。这次应该差不多。如果还有时间,我会陪着我的孩子,督促我的女儿学习。
(应被申请人的请求,文中的宁美是化名)
来源:BBC新闻网
标题:“我离开女儿来到武汉,正是为了更多母女相聚”|疫情下的“她力量”
地址:http://www.0bbc.com/xbglxw/12023.html